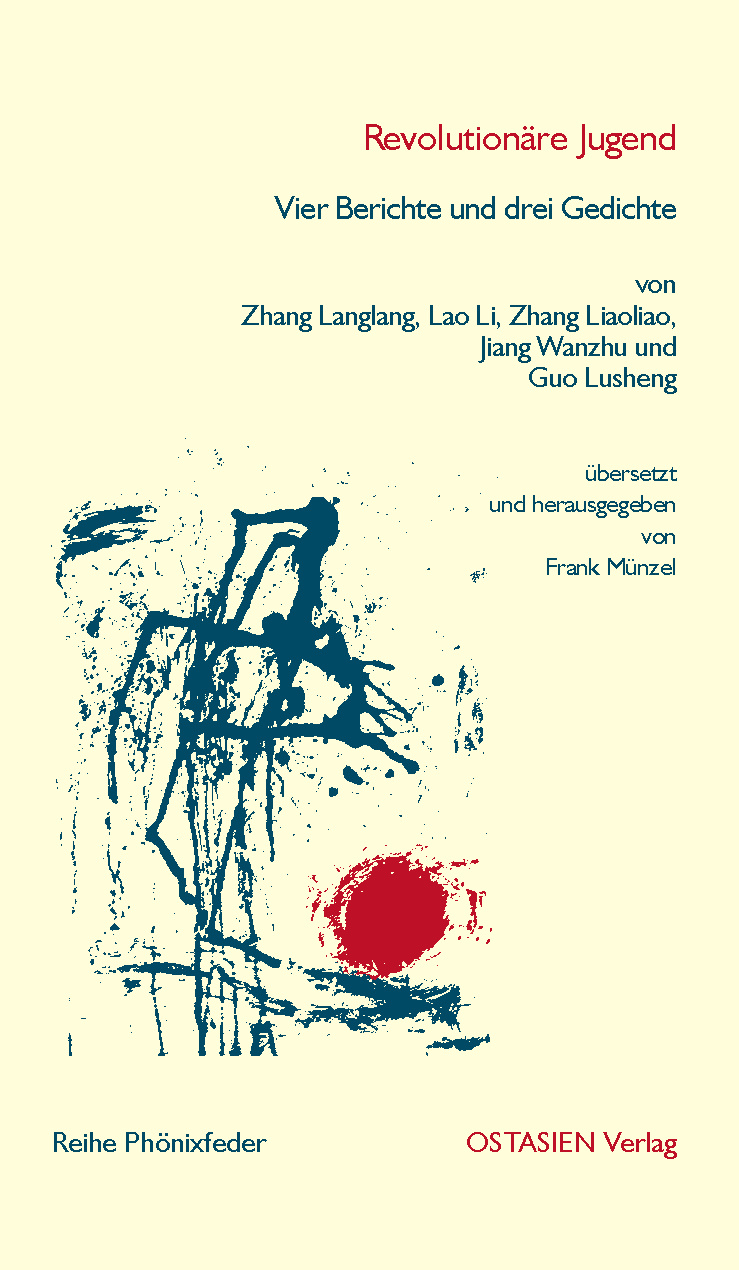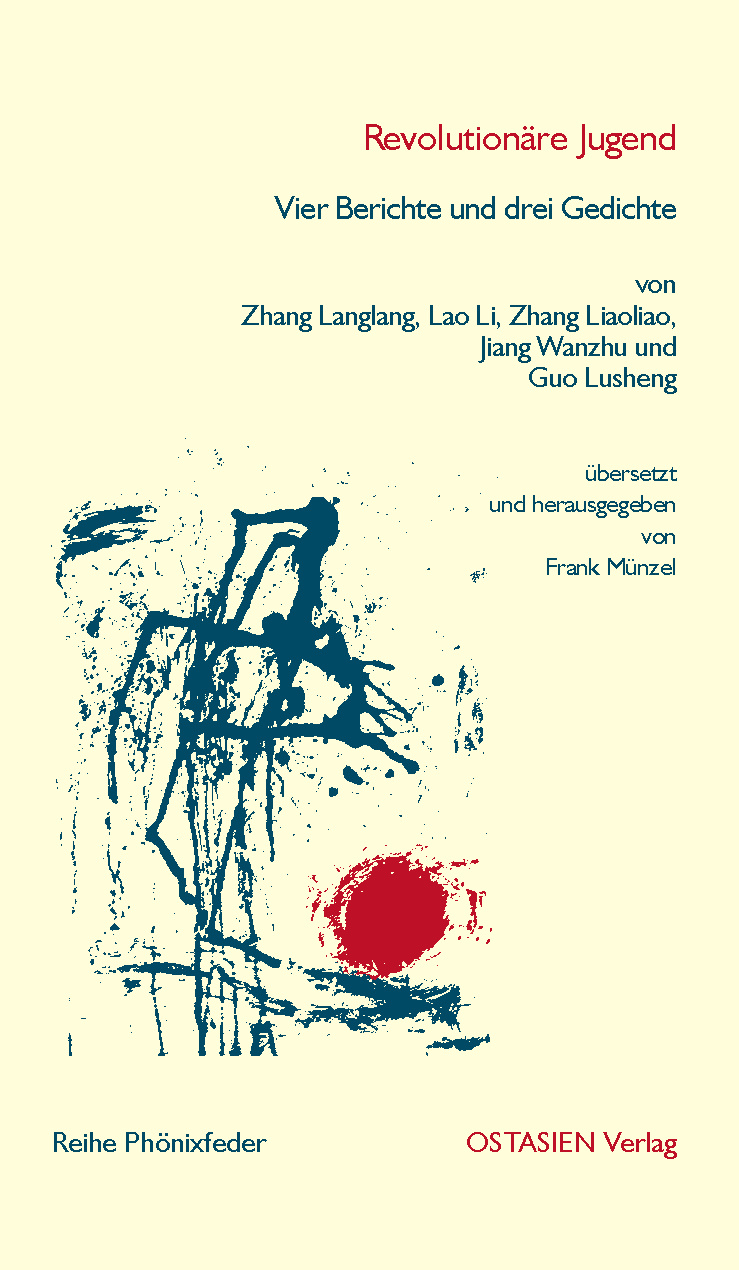一
如果把中共建国以来对思想控制松紧的程度, 画成一条曲线。 我以为, 一九七零年初的 “一打三反” 运动就是曲线的顶点。
建国后至少有了宪法, 有了法律程序。 思想控制, 一张一弛;基本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 一般人们记得的不外是 “反胡风” 了、 “反右” 了、 “文革” 了等。 然而, 在全国范围内, 大规模的以言论罪(即 “思想罪” )通过公审程序, 正式判处死刑, 似乎还应该是 “一打三反” 。 可惜, 在 “邓小平思想” 的 “向前看原则” 下, 这么重要的里程碑, 被刻意遗忘了。
现在, 当局不准回忆文革, 最近对国内的媒介明文规定若干个 “不准” 。 “一打三反” 这个词, 几乎快没人明白了。 人们在纪念遇罗克的时候, 才有人提起这件事情。 作为历史的一个符号, 遇罗克远远大于 “一打三反” 。
“一打三反” 是当局最疯狂的时期, 中央居然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 审判不需要最高法院认定, 认定死刑犯不需要有人命或纵火等严重罪行。
全国各地都在成批地枪毙 “现行反革命份子” 。 而他们主要的具体罪行是: “反动标语罪” (书写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标语等)、 “反动口号罪” (在公共场合呼喊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口号等)、 “恶毒攻击罪” (和他人谈论过对领导人的不满或不敬的言论)等等, 这些都可以判处死刑;甚至连 “反动日记罪” (在日记中表达自己对当局不满等)都可以判处死刑。
一贯注意政策的首都北京, 在这几个月中, 天天到处是游街和批斗死刑犯的镣铐拖地声, 腥风血雨满街充斥 “枪毙XXX!” 的口号声, 到处贴着画满红钩的死刑告示, 一批批政府制定的 “斩监侯” 名单, 要求 “全民讨论” , 让普通百姓人人表态, “自愿” 成为裁定者之一。
我事后知道, 在讨论枪毙我的时候, 逃离现场拒绝表态的至少有画家黄永玉、 画家刘迅(现任北京 “国际艺苑” 董事长)。
这比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 要厉害得多, 风声鹤唳, 人人自危。 因为, 一句话就可以定罪, 谁保证自己没说错过话? 其他城市和地方就更残酷了, 河南省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因为说过两句反对毛泽东的话,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先生, 因无法忍受残酷批斗, 而 “呼喊反动口号” , 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一打三反” 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 每个案件真实情况如何? 今天被深深封存入黑箱。 已经二十九年过去了, 是否人们真的就此忘记了?
历史不那么健忘吧?
二
当时我也进了死刑号。 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 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 “太阳纵队” 有关。 前者属于 “乱说” , 后者属于 “乱动” 。 前者是企图 “言论自由” , 后者是企图 “结社自由” 。
我 “犯罪” 时间是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 入狱时才二十四岁, 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那时, 实在天真, 误以为这两项自由是我国宪法白纸黑字规定的 “天赋人权” , 是从毛泽东到朱容基们 “冒着生命危险” 为我们奋斗得来的。
哪知道这两条正是当权者的不可退让的底线。
我不入狱才怪!
后来, 从死刑号逆向出来, 逃出生天简直是个奇迹。 我当时根本不认为, 自己还有存活的机会。 据说, 把我从死刑号里提出来, 转到普通牢房的老军代表是李振先生。 当时他说得很清楚: “进死刑号的人, 没有活着出来的。 你不用感谢我, 要感谢党中央, 感谢毛主席。” 他又说: “有关死刑号的一切都是国家机密。 你不许向任何人, 谈死刑号的情况。”
有人告诉我, “一打三反” 的得力执行者和知情者正是李振先生。 在全国杀人杀红眼的时候, 周恩来突然问李振: “谁给你的尚方宝剑?” 据说, 因此, 一九七零年五月以后, 杀人的势头慢慢缓和下来。 据说, 不杀我们也是周恩来的帮助。 我在监狱时, 一直想: 出来后一定拜访他们, 要知道事实真相。 可是等我出狱时, 他们二位都已经作古了。
我还想继续追索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所以要写这一类文章。
同时, 还由于我和其他死刑犯, 在死刑号曾经相约: 谁万一能活下来, 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 要去问候死难者的家人。 和我一样虎口余生的人还有, 可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 愿意选择沉默。 我现在是个单身的职业作家, 没有什么牵挂。 我正在继续写这些经历, 想留下个人的些许见证。
让后人多些第一手资料, 以便研究。
三
我们那一批死刑犯, 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宣判。
我记得名字的有: 遇罗克、 田树云、 孙秀珍、 沈元、 索家麟、 王涛、 王文满、 朱章涛等。 最后两位的下落, 我至今不清楚, 其他都立即执行了。 被枪毙的思想犯中, 当时最有名的就是遇罗克, 他是以一篇 “出身论” 反驳当时同样有名的谭立夫(比较讽刺的是, 谭先生现任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的 “血统论” 演讲。 这讲演的核心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是当时红色恐怖的理论依据。 “出身论” 喊出弱者的心声, 曾一时洛阳纸贵, 家喻户晓。
而知识界最有名的是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青年才子沈元。 因为他被批斗、 殴打而无法忍受, 化妆成黑人, 跑进了马里大使馆, 被定为 “叛国投敌罪” 。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游戏规则照搬不误。 对我的罪行认定分三个层次进行:
1、 公布罪行: 这是造舆论用的。 多半要和 “叛国罪” 、 “暴乱罪” 等挂钩, 激起公愤。 就可以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 所以, 把我和法国留学生马丽亚娜(后为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副校长。 )、 郭翰博(后为巴黎《世界报》记者)聊天, 定罪为 “出卖重要情报” 。 我曾想去法国留学, 被追捕时曾想去香港, 定罪为 “企图叛国投敌” ;
2、 具体罪行: 这是判罪的表面原因。 例如: 写了犯上的文字, 或卷入什么文人作乱的案件。 到 “一打三反” 广泛多了, 例如: 说过中央领导人的隐私或不满等, 不需要物证, 只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听见此人说过这句话, 就可以定罪。 我因为说过诸如: 毛泽东先生的 “七律” ( “暮色苍茫看劲松” )可以作香艳解等笑话, 定罪为 “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 ;
3、 实质罪行: 毛泽东说: “罚不当罪的极少” , 在法制极不健全 “一打三反” 时期, 中共还可以 “稳、 准、 狠” 地枪毙思想犯。 如何 “准” 地定罪呢? 许多人都想不明白。
平心而论, 中共这时, 已经不在井冈山, 很成熟了。 并非抓来就打靶, 那就小看了中共。 至少北京还是相当认真的。
从思想定罪来说, 他们很有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们抓我没有抓错。
四
程序是这样的:
1、 根据密告、 或眼线的线索, 先把思想犯嫌疑人列入档案, 行话说: 挂号了。 一九六五年俞强声(俞正声部长的胞兄)在北京公安局一处工作(据报导现叛逃美国——编注), 他透露给一位朋友 “张郎郎已经挂号了” , 如毛泽东说: “入了另册” ;
2、 公安干警和眼线有目的搜集被锁定的目标所作所为, 非常细致, 例如: 后来在我的判决书上写道: “在公共场所播放反动音乐” , 是指我和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 在后湖放过 “披头四” 的歌曲。 可见, 他们对我们的 “反动文艺思想” 侦察多么细致。 前不久陈庆庆小姐对我说: 文革前她爸爸(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先生)就拿内部参考上对我 “资产阶级思想” 和行为的描述, 作为反面教材对她进行教育: 长大了千万别学他。 那些 “材料” 全是我在学校的生活细节, 例如: 把游泳裤钉在墙上等等。 事实真假姑且不论, 可见跟踪思想异己的眼线, 那时已经深入在学校中。
党什么都知道。
3、 发现或制造具体罪行, 然后抓人。 一九六八年初, 当江青女士说 “中央美术学院有坏人” 的时候, 她肯定不是具体指我, 可是我已经是 “被锁定者” 。 在北京公安局的参与下, 在各艺术院校半年之中私设公堂、 血腥逼供后, 根据被拷打者的 “供词” , 经精心筛选, 我就堂而皇之成了 “头号反革命” 。
4、 逮捕以后要认定 “罪犯” 思想反动的程度, 和目前的思想状况, 即: 所谓 “态度” 就是对领导人的态度、 中共的态度。 也就是说: 在判处思想犯的时候, 主要就是看他的思想罪行的深度和可否改造。
在预审处管辖下的看守所, 有专门主管思想犯的有经验的预审员, 而负责我们这类 “疑犯” 的预审员, 文化水平就高一些。 对付读书人很有办法, 进行逼供、 诱供。 要找出所有的 “罪行” , 最后还要找出 “思想根源” 和 “原始动机” 。
他们非常重视你家里有没有被当局 “关、 管、 杀” 的? 或者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家里有没有受到冲击或牵连? 可见, 中共当时对思想犯的心理历程非常重视。
他们要分析我们每一个人, 如何由拥护党到反党的全过程。 这样可以明白 “思想犯” 形成的前因后果, 就可以决定我们的反动 “程度” 。 还可以用来防止别人走上思想犯罪之路, 通过 “狠斗私字” , “灵魂深处闹革命” , 防患于未然。
五
许多人觉得 “思想” 看不见、 摸不着, 如何定罪呢? 中共凭多年经验界定思想罪行, 有很具体的办法。 例如:
1、 如果罪行本身到了一定的级别, 无需验证就可以定罪了, 如北京挑花厂的厂医田树云, 写了一封信, 扔进前苏联大使馆的汽车里, 想投靠 “苏修” , 那已经 “反动透顶” 了, 所以不必再界定他的思想反动程度了, 立刻可以枪毙了。 可是, 田大夫很天真。 在批斗换场时, 他安慰我说: “马队长对我说了, 咱们是批判从严, 处理从宽。 别听群众都喊要枪毙咱们, 咱们死不了。” 我只能苦笑。 他太相信党了。
2、 如果罪行一般, 可是 “态度恶劣” , 一样可以枪毙。 比如: 上述田大夫的女朋友孙秀珍, 她的罪行最多是 “胁从” 或 “知情不报” 。 据说, 由于在 “公判大会” 上, 她企图抗拒, 呼喊口号, 也同场枪毙了。 因为, 她的态度说明她 “死不改悔” 。 遇罗克的预审员丁先生(外号丁大个儿), 早就认定了他 “反动透顶” , 可是, 表面罪行还不够, 结果等到了 “从重从快” 的 “一打三反” , 合理合法地枪毙了他。
3、 组织是思想反动等级的一个界定点。 当时成百成千的人说过错话,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们呢? 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们有个组织, 而且并被认为是个思想异端的俱乐部。
他们的方法还要精确得多, 复杂的多;我凭直觉感受到这些。
六
在文革前六十年代已经有许多人喜欢写诗, 实际上有很多小组, 可是被当局认定为成型的组织, 一个是郭世英组织的 “X社” ,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艺术沙龙 “太阳纵队” 。
我和郭世英是101中学的同学, 在学校里都是文艺活跃份子, 在记念鲁迅的晚会上他扮演过客, 我导演《祝福》。 我们在一起合作很愉快, 聊了很多。 那个时候由于年轻人的偏激, 我很不喜欢他的父亲郭沫若老先生, 主要是嫌他没骨气, 写的诗又不好, 那时哪知道他的难处。
后来郭世英上了北大哲学系, 我去了中央美术学院, 各自组织了沙龙。 一九六四年当局发现他们 “X社” 策划去法国, 结果, 一人成功出走, 其余全部落网。 好在当时社会还算稳定, 郭老先生又身居高位, 他们没有被判刑。 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 然后转往农业大学读书。 可是, 噩运并没有结束, 一九六八年郭世英被隔离审查、 毒打。 一天, 郭世英从二楼摔下来死亡。 当时他还被绑在床上, 他妹妹赶来收尸的时候, 还没有松绑。
人们说是自杀, 家属说是他杀。 前不久, 我在北京和郭世英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周国平(现在继续研究哲学)、 牟筱白( “X社” 和 “太阳纵队” 的成员, 诗人)回忆过这些。 他们也认为: 根据他的性格, 决定了他一定会在那种情况下自杀……。 总之郭世英为写诗付出生命。
郭老先生的另一个儿子郭民英, 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 在他哥哥死后, 很快也自杀了。 文革后郭世英留下了一本日记, 郭沫若晚年经常拿出这本日记, 用蝇头小楷一笔一笔抄完这本日记。 (关于郭沫若两个儿子之死, 请参阅本期下附罗点点撰〈郭沫若的两个儿子〉——编注)
“太阳纵队” 成员的命运不比 “X社” 的强。 “太阳纵队” 一九六二年成立时参加的人有张久兴、 张新华、 董沙贝、 于植信、 张振洲、 杨孝敏、 张润峰等。 由我起草章程。 那时还是太年轻, 不知天高地厚。 我在章程开始说: “五四” 过去这么多年只出了一个鲁迅。 当时膂b为 “五四” 出了不少盗火者, 现在不知去向。 我们也是心中有魔鬼在燃烧, 我们也要象高举燃烧的心的丹柯一样, 走出黑暗和泥沼。
先后卷入 “太阳纵队” 或和我们沾边的人, 都受到各种冲击。 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 张久兴文革时在军队, 已经是坦克兵的军官, 在军法处逼供下承认另一个莫须有的 “叛国集团” , 后自杀身亡。
甘露林也是解放军军官, 正在广西向越南开赴, 接到回北京接受审查的命令, 他在前线饮弹身亡, 和郭世英一样;人们说是自杀, 家属说是他杀。
我和一个不愿提他姓名的朋友进了死刑号, 在大狱中九死一生。
于值信先在天堂河农场劳改, 后送到新疆石河子农二师, 文革后一直下落不明。 前两年我和吴尔鹿找到了他, 可是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不能在社会中自理的人。
……
任何和 “太阳纵队” 沾边的人, 都被批斗、 管押、 审查。 后来, 只要和我接触过较多的亲戚、 同学、 朋友几乎无一幸免。
例如原北大英语系的毕业生杨孝敏, 因此案一直下放在工厂里, 不得翻身。 我女朋友蒋定粤的哥哥蒋建国先生, 因我被打穿耳膜。 蒋定粤的妹妹蒋定穗, 脸上至今留下刑讯用烟头烧下的疤痕, 等等, 等等, 等等。 被牵连的名单数以百计, 使我至今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深深负疚。 虽然, 这不是我故意造成的, 也不是我能改变的。 但确实是因我而起, 希望他们能够谅解。
“太阳纵队” 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没有什么政治诉求, 最多就是想写诗、 画画, 要创作自由。 说破了还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事。
我希望, 在下一世纪, 可以在祖国实现三十多年前我的小小诉求。
原载《民主中国》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